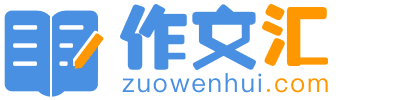在求学的道路上,写作文往往是一件令人头大的事,经常不知道怎么写,但必须清醒认识到:拥有好的文笔,绝对是受益一生的硬实力。而写作能力的提升,必须从小培养,对于这篇作文题目,建议多看《我记忆中的过年》相关范文,多动笔练习《我记忆中的过年》相关习作,相信功夫不负有心人。本文由作文汇用户投稿,希望为你的写作带来帮助,如果觉得这篇我记忆中的过年作文2000字不错,记得推荐给同学哦~
“是猪闯了祸在挨打吗?”我问娘。
娘说:“瓜娃,那是人家杀年猪,快过年了。”
娘用竹竿从房檐下挑了一串柿饼缓缓放进簸箕里,每个柿饼都像在面柜里滚过,白花花的。
娘说,今年这柿饼霜厚!我不懂,霜在哪?娘说,柿饼上跟白面一样的就是霜。我更疑惑了,那太阳照着咋不化?
娘给我解释:柿饼上的霜跟地上的霜不一样,它是柿饼本身发散出来的,柿饼上的霜越厚,柿饼就越好吃。
我馋了,马上就想吃。娘从柿饼串子上摘下一个放到我手里,我还想要,娘却说:“柿饼不能多吃,吃多了肚子疼,先尝一个,其他的留下等过年时再吃,过年来客了还要给客吃。”
“过年,啥时候才过年啊?”我有些着急。
娘又去挑另一串柿饼,“快了,你听人家都开始杀猪了。”
我问娘:“那我们咋不杀猪呢?”
娘说:“我们的猪都卖了,拿啥杀哩,你晓不得你爷忌口,我们一直不吃肉?”
“哦,那我想去看人家杀猪的,能行吗?”我跟娘说。娘不让我去。
这时婆(婆,即祖母)从水泉里提了一圆罐水走上了门口的石阶,听到了就给我帮腔说:“娃想看去就让看去,娃没见过么,他大(大,指父亲)也可能在那儿给人家帮忙着哩。”
娘瞅了我一眼说:“那你去吧,去了听你大的话,离杀猪的远点,不要到处胡摸乱蹭,别把棉裤和袄弄脏了。”
我咬了一口硬邦邦的柿饼,高兴地朝庄子中间奔去。在河边柳树下遇到我爷,他正用篼篼和锄捡拾路上牲口拉的粪,看见我就问:“干啥去?”
我说:“看杀猪的。”
爷说:“那有啥好看的。”我没管,只顾往人多声杂的地方跑。
杀猪的是后院安顺家。我和安顺是好朋友,他每次放羊都会叫上我,我家虽没羊可放,但我乐意跟着他,都是娃娃伙的,聚一起好玩。只因他比我大一两岁,娘还让我称呼他安大哥。当然,背地里我一直都叫他安顺。
安顺已经看见我了,激动地从门前的斜坡上往下跑:“快点来,我们家今天杀猪,等一阵开膛了,取出尿泡我们吹着耍。”
院坝里的几个大人都给惹笑了,其中一个说:“对着哩,又来了个吹尿泡的。”
大正站在他们中间端着搪瓷缸子喝水,我抢先跟大说:“大,我来看杀猪的。”
大还没开口,不知是谁喊着我的小名戏谑道:“来迟了,来早些还能帮忙拉扯一下猪。”
“猪早杀了,烫都烫毕了,你看,已经上架了,歇一下就开膛卸肉哩。”大指着院坝中间的一个木头架子给我说。
这时我才注意到,杀了的猪端溜溜地倒挂在架子上,毛已经拔光,裸露着白亮亮的皮肉,脖子那儿有个刀口,还在往外渗血。杀猪原来是这么恐怖的一件事,我呆呆地看着,心里有些害怕。
安顺却显得很欢快,他拽着我去看烫猪用过的大木桶,说:“猪杀了要先放进桶里用开水烫,烫了才能拔毛。”
安顺又给我介绍木桶旁边的一张矮桌,说:“这也是杀猪用的,帮忙的人把猪按在桌子上,杀猪匠就在桌子上把猪杀了。”
我想,杀猪匠咋这么毒呢,那边就开始闹腾着:“开膛,开膛。”
杀猪匠手执屠刀,割下猪头,然后划开猪肚子,掏猪的内脏,他在里面翻了几下就割了个小肉囊给我,还说:“这就是猪尿泡,拿上耍去,好像还有点尿,先把尿倒了。”我不敢接,安顺过去接了,又拉我到旁边去玩。
安顺果真从猪尿泡里倒出一些尿,一股骚臭味马上四散开,我立刻放弃了玩猪尿泡的想法。
安顺却很来劲,嘴对着肉囊的口子往里吹气,囊就渐渐鼓起来,鼓到囊壁透亮时,安顺在尿泡系那儿打了结封住口,尿泡就很像白气球。
安顺把这个白气球抛到空中,我们追着打着闹着笑着,庄里别的孩子也来了,围着猪尿泡做成的气球疯玩。
玩累了,一群孩子就横七竖八地躺在老刺槐树下面的碾盘上。碾盘经常不用,落满了尘土和草屑。
贵成家厢房的墙角上安个石碓窝,四财瞅了一阵对大伙儿说:“你们看,碓窝跟锅一样,我们找些土当面,折两根棍当筷子,再舀些水,在碓窝里搅面茶耍。”
我说:“四财,那在贵成家门边上,你问一下看人家愿意不,小心贵成他娘骂人。”
贵成说:“好的,我娘不骂。”
安顺却对贵成说:“不骂才怪,我看昨天你娘刚把碓窝洗了,准备要在碓窝里踏(捣)调货(调料)哩。”
安顺又大声提醒我们:“四财在碓窝里搅面茶让他搅去,我们不要参加,快过年了,庄里家家都要用碓窝踏调货,谁把碓窝弄脏就要让人骂死哩。”
“让四财一个人搅去,我不搅。”
“我也不搅”……伙伴们都表了态,把瘦小的四财晾在了那儿。
四财一边离开石碓窝一边嘟囔着:“不搅就不搅嘛,我也不搅了。”
我们刚从碓窝边撤开,就看见贵成他娘抬了一筛子炕干的红辣椒从门里往出走,她一眼就看见了这边的贵成,张口喊道:“成娃,别耍了,到屋里来,把酸菜桶跟前放的碓窝里用的石杵子拿出来,给我帮忙踏辣椒。”
贵成努着嘴朝她娘走过去,我们都嘻嘻哈哈笑起来,四财把舌头一伸做了个鬼脸说:“老天保佑啊,幸亏我们没在碓窝里耍!”
不觉已到了饭时,各家的大人高声吆喝着自己孩子的名字,叫娃回去吃饭,伙伴们都散开了。
安顺拉了我一把,说到他家去吃猪肉,我大还在他家里,新猪肉可能都煮好了。
吃猪肉只算个由头,和安顺能再乐半下午才是主要目的。
我和大从安顺家回去,没进门娘就开始指教我们:“一个帮忙杀猪的,一个看杀猪的,实诚得很,把肉给人家吃完了才回来哩?晓不得自己屋里的忙紧。”
大却反驳道:“说的那啥话,帮忙就要帮到底,人家留下让吃点肉,走了也不好看嘛。”
“哐哧”一声,碎爸(碎爸,父亲的小弟)把他刚背回来的一背架子柴倒在门前竹林边。碎爸这个冬天有空就去背柴,他背的柴已经攒了高高一大摞子。
婆把一部分柴已经架到灶房的棚杆上让烟熏着,熏干的柴更容易烧着。婆心疼碎爸,说柴够烧就行了,没啥烧了再背。
然后婆走过去,给那群鸡撒了一把粮食,又叫我说:“云娃,我们去竹林背后看看牛吃剩下的包谷秆多不多,抱上些放在几个炕眼门上,天黑了好烧炕。”
我说:“婆,我想喝点开水,渴得很。”
爷拿把镰刀准备往竹林里走,听见了就笑着问我:“你把肉吃得多了吧?”
我说我只吃了几小口,又问爷:“拿镰刀去干啥,要剁竹子?”
他说:“剁根竹子,劈些蜡棍子,年跟前了,要灌蜡哩。”
牛啃过的草秆子不多,婆说只能烧两个炕,还得到牛圈楼上扯些麦草添补点。
吃过晚饭天就黑了,碎爸点着了厅房大柜上的罩子灯,灯里面的油已经不多,他从大柜腿腿那儿找出煤油瓶给灯加了点油,然后又去拧收音机,但拧了半天都没调出个清晰点的台,咔咔吧吧地乱响,等到能听了声音又太小,播音的人像卡着一口痰,说的很不利朗。
爷靠着柱子歇息:“收音机可能没电了,换过电池已有两三个月了,我手电里面的电池也老了,打起来跟火柴头一样黑哇哇的。一对电池要好些钱哩,都难养活啊!”
“电池老了能换,人老了莫法换,人老了莫火气,炕烧不热都不敢睡,烧炕,烧炕。”婆边说边往炕眼门上蹲。
我说:“婆,我烧,你歇噶(歇噶,歇一下)。”
婆高兴地摸着我的头:“那你烧,我看你能行不。”
我先往炕眼里架了几根短点的包谷杆,然后擦火柴燃着一个包谷叶苞,把它缓缓地放在草秆底下,火就慢慢烧大了。
婆夸我:“云娃攒劲!明天逢场,我引娃赶场去,年跟前了,场欢得很。”
窗外刮起一阵风,屋后青冈树林里没落尽的干叶子哗啦啦作响。
腊月的场有两个特点:货多,赶场的人多。我赶场最喜欢的是卖年画的摊子,明星画,风景画,电影宣传画,地上摆的,靠墙挂在拉绳上的,我都会久久驻足,一一过目。
年节前,很多人家要贴年画,年画贴在屋内显眼的墙壁上,自己看,来客也看,画的内容常成为人们闲暇时的谈资。贴年画的墙要用报纸糊过,因此腊月的场上便有不少卖废旧报纸的,一摞报纸,再放一把带盘的杆子秤,不用吆喝,就有人来称。
杀了猪但缺钱用的,也赶着年末最后几个场把自家的猪肉拿来交易。猪头,猪腿,猪排骨,猪的心肝肺,还有肠肠肚肚就沿街摆开。
铁匠卖刀斧锄䦆,木匠卖桌椅柜橱,篾匠卖竹席背篼。
拔牙的,算命的,打着空翻卖武的,理发的,杂耍的,倒腾狗皮膏药的。
更有那油盐酱醋茶,衣帽布鞋袜,干湿果品,杯碗瓢盆,菜蔬糖酒,饮食干粮,从东街到西街,从南街到北街。
还有卖炮仗、香灯火烛和天爷地爷门神爷灶王爷彩色版画的都在当中挤着,人乐,神也乐。
整个场上,各色的货物铺天盖地,琳琅满目,各类的赶场人,欢欢喜喜,摩肩接踵,腊月的场就这样热热闹闹红红火火。
我想买几张年画,婆却弹嫌说:“画让人家糊墙的人买,你不糊墙,晓不得啥样的好。我看上的有鱼有胖娃娃的画,人家都看不上。”
我闷闷地说:“那种我也看不上,那你给我买炮。”
婆说:“买炮还早么。”
我求着婆:“先给我买一盒。”婆答应了,好好好,给娃买一盒。
婆就给我买了一盒电光炮,说是一盒,其实并无盒子,是七八寸长的串串,外面包裹着一层深红的油光纸,还贴着花花绿绿的标签,一看就让人喜欢。
婆叮嘱我:“放的时候拆开一个一个放,不要都点着,都点着一口气响完就没了。”
我说:“我知道,我才不让它一下子就响完,我要少少放。”
我还想在场上转几圈,婆却要回去,说今天天气好,淘点磨磨(淘磨磨,淘洗用来磨面的粮食。)干得快。
跟婆回到家,见娘和大把磨磨已经淘完了,娘从河边往回收拾淘磨磨用过的锅笸和笊篱,大在晒场上拿长把木耙翻搅着两大席湿麦子,耙齿划过,摊在席上的粮食就出现一道道浅浅的沟槽。还有一席是雪白的玉米。
我问娘:“今天咋淘这么多磨磨呢?”
娘说:“预备打(磨)年面的,快过年了,蒸馍做饭,要好多面哩。”
哦,我应了一声,跑去要大手里的木耙:“大,我也想搅。”
大却拒绝了,说我不会搅,一搅就会把粮食弄到席外边。我只好悻悻地离开,往屋里奔去。
爷正在厅房的小桌子上劈蜡棍儿,我马上兴冲冲地给他炫耀我的炮,爷忙说他身边有火盆我拿着炮要离远一点,爷还让我把炮先压在炕席下面,说炕上暖过的炮声音才更大。
我就把炮压在炕栏边的苇席下,我胆子小放炮还得爷看着,所以放炮的事我都听爷的。
爷劈蜡棍时戴着眼镜,他那眼镜我曾经试着戴过,结果什么都看不清,还觉得有些恶心,爷说那是老花镜,专给老年人戴的,娃娃的眼睛没毛病戴着肯定不舒服。
透过镜片,爷很小心地把一节一节的竹子劈成一根根细细的棍棍儿,爷把它叫蜡棍儿,爷将这些蜡棍整整齐齐地码在一页手工纸上。
我想取一两根蜡棍当玩具,爷却不让我动,他说蜡棍灌蜡敬神,我的手到处乱摸不干净。
不让动就不让动嘛,我找我的老黄猫去。
老黄猫在炕上,我知道把铺盖撑起个大包的就是它,过去掀起来果然是它,我叫:“猫儿猫儿,起来。”
它蜷得紧紧的不理我,我就亲热地把它从头摩挲到尾,可它眼都不睁,反而呼呼噜噜打起了鼾。猫的鼾声抑扬顿挫柔和淳厚,不断反复如同乐曲。
关于猫的鼾声,婆给我讲过一个故事:猫原来住在天上,因为人间老鼠太多,粮食难以储存,上天就派猫来帮人除害。猫下凡后很勤快,不久便捕捉了大量的老鼠,有力地打击和惩治了鼠害,猫觉得它可以交差了,人们应该送它回去,但人们担心猫离开后老鼠会再次猖狂,就没急着送它走。
从此,猫歇下来就念叨:“让送不送,让送不送。”听,我家老黄猫这阵子正呼噜着这一句呢。
“别糟蹋猫了,让睡去,猫昨晚上捉了只大老鼠,乏了。”
我正捋着猫的长胡子,婆发现了就大声劝阻我。婆这一惊,老黄猫站起来伸了个懒腰跳下炕跑出了门。
我对婆特怨恨:“都怪你,把猫吓跑了!”
当我转回去再看爷时,他已经开始给那些蜡棍缠棉花,薄薄的一层棉花缠裹了蜡棍三分之二的身子,顶端还拧出一小段细细的棉绳当捻子,那些缠了棉花的蜡棍叫蜡芯,灌蜡就要灌在蜡芯上。
爷说腊月二十三就要送灶爷,他今天得赶着把蜡灌出来。
吃过晌午饭,爷在火盆里煨了一个大茶罐,里面汆着半茶罐水,等水稍微热了一点,爷先把掰烂的黄蜡块轻轻放入茶罐,然后他又忙着把那些做好的蜡芯子一个一个地插在大萝卜切成的圆台上,萝卜是爷提前选好洗净的。
每块萝卜上大约要插十根蜡芯,蜡芯须插得一样高,这样灌出的蜡才一样长。相邻蜡芯之间的距离不能太小,也不能太大,灌大蜡,蜡芯和蜡芯之间的空隙就应该留大,灌小蜡,这个空隙也就应该留小。
爷十分认真地插着每一根蜡芯,像完成一件工艺品。这期间,爷还要注意观察茶罐里黄蜡的熔化情况,等那些固态的黄蜡完全熔化以后,爷就把茶罐往火盆边上退一退,朝着茶罐口嘘嘘地吹气,像给我说,也像给他自己说:“凉一凉就能灌了。”
我问爷:“那些黄蜡块都化进水里了吗?”
爷说:“是化了,但它比水轻,所以漂在水上面。”
然后爷就不让我吵了,他小心地拿起那些插着蜡芯的萝卜块,翻转,将蜡芯齐齐地没入茶罐中。待液面刚好淹过蜡芯上的棉花层时,又立即缓缓地提出,原来雪白的棉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层光滑润泽的黄蜡。爷再嘘嘘吹着,把它放回原处,接着灌另一块,如此反复。
灌过一遍的等凉好了再灌一遍,小蜡要灌三到四遍,大蜡更多,罐子里的液面渐渐下降,蜡烛也眼见着胖大起来。
蜡灌好了,爷还要消蜡头,就是把被糊住的蜡捻子消出来以方便点燃。
消蜡头不用茶罐,用炒调货的马勺,把马勺放在火上面烧,烧热了,将灌好的蜡烛的头头儿在马勺里轻轻地蹭,裹着捻子的那点蜡一化就得停住,时间过长反而会破坏蜡烛的完整。
蜡头消完,爷找出一个长方的纸盒,把那些金黄油亮的新蜡烛放进里存好,灌蜡的事情就算完成了。
记忆中,过年前后最忙的是娘。
娘白天干家务,晚上还要抽空在油灯下用脚踏缝纫机给我赶做过年穿的新衣裳。娘不停地忙着,缝纫机不停地响着,机轮嗡嗡,针脚噔噔,嗡嗡嗡噔噔噔。我已经在炕上睡着了,娘还在干活。
或许就在第二天,娘突然把我叫过去,让我试穿她给我新做的衣裳,还从箱子里翻出刚刚上好的布鞋,说都试一下,有毛病了她赶快改,没毛病了先放下,等过年时再穿。
年啊,我真的好想过年。到底啥时候才过年啊?
娘说还有六七天,今晚上就送灶爷哩。
我说,把灶爷送到哪里去?娘说灶爷要回天上去。
我担心灶爷再不回来,好在娘又说,三十还要把灶爷再接回来,我心里才踏实了。
送灶爷需要给灶爷备干粮,二十三这天娘早早地就开始和面发面,着手给灶爷烙饼,一年十二个月就要烙十二张饼。
烙好的白面饼散发着独特的麦香,我很想吃,娘却说送完了灶爷我才能吃。
我就疑惑了:“送完灶爷,饼不是都被灶爷吃了吗?”
娘笑起来:“灶爷吃不吃,到时间你看着,如果他不吃,那这些饼你想咋吃就咋吃。”
我不奢望灶爷一个都不吃,毕竟上天去那么远,不吃点怎么行。不过,他老人家如果能留一两个给我,那该有多好。
我盯着灶台墙上那张旧年的灶王爷版画,默默地祈祷着,画上的灶公灶母慈祥和蔼,身边还围着可爱的家禽家畜。
送灶爷的事具体由我爷完成。晚饭后,爷在那张灶爷的版画神像下面点起了香灯,然后又烧供茶,一拃长的个小茶罐,烧的清茶刚好能倒两小盅。
爷双手端起供茶举过头顶,缓步上前,把茶恭恭敬敬地放在香灯前,再退下用干净的盘子装了白面饼,和供茶一起给灶爷献上。
昏黄的烛光照亮了灶爷像,也照亮了我爷在灶台下面磕头作揖再磕头再作揖的无限虔诚,于是我也学着爷的样子磕了两个头。
最后,爷带我去放炮,说灶爷要走了,应该放炮送一送,我自然很高兴。几个炮放下来,我把吃饼的事竟忘了。
隔了一夜,喝早茶时,我才记起那些白面饼。
我问娘:“灶爷走时把白面饼留下几个没有。”
娘笑着说:“留下了,都留下了,我已经收捡到笼子里了,现在就给娃拿。”
送走了灶爷,家里开始扫霉尘。所有住房,楼上楼下,里里外外,蜘蛛网、灰尘,都要清理打扫一遍。
为了防粘霉尘,各样家什能遮盖的一律盖上,不能遮盖的就暂时搬到屋外,碗盏水壶,盆盆罐罐,在门外台阶上摆得乱七八糟。
大和碎爸一人拿把长扫帚,从天棚到楼板,从墙上到脚地,各个圪崂角角,都彻底地打扫着,屋子里一时间乌烟瘴气,充满了呛人的霉尘气息,黑乎乎的霉尘落得到处都是。
我还想伸着脖子看看,大却厉声斥责道:“出去,出去,灰尘大得很,太喷了!”我就怯怯地退到屋外。
打扫到低处以后,娘和婆也参加上了,又扫又擦抹,再把各样物品放归原位,这个过程比较慢,耗时很长,因此这一天的午饭做得就很迟,我饿得心都发慌了,还吃不上饭,娘便让我先吃几口馍,我却嫌馍又冷又硬不想吃。
但当我看见大和碎爸被喷的满身的霉尘,连鼻孔里也沾满了黑乌乌的霉尘的时候,就不好意思再喊饿了。
扫过霉尘,年前要做的事就一件赶着一件,灶火里的最复杂,泡黄豆做豆腐,泡荞麦做凉粉,蒸馍馍,蒸包子,煎面疙瘩……
因为爷皈依佛门吃长斋,多年来家人已习惯了用素食,所以我家过年不做肉,饮食比别家就简单得多,但面一定要准备宽裕。
水磨时代,磨年面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水磨效率低,磨面的人又多,为了磨点面经常得放夜。后来有了钢磨,磨面就不用发愁了,把淘好晒干的磨磨装上架子车拉到磨坊,即便是排队候着,时间也不会太长,少半天就可以解决问题。
腊月二十五六以后,没啥忙活的家里就有开始刷墙的,刷墙并不是用刷子蘸着灰浆刷,而是用纸糊,糊墙的纸有麻纸、白纸,慢慢才演变为报纸,有些讲究的人家,还会把顶棚、梁柱这些眼前能看见的地方都糊一糊,墙糊好了就贴年画,挂中堂。中堂的内容多以毛主席像为主,也有用纸在当中竖着写了“天地君亲师之位”的。
经过这么一番装饰打扮以后,陈旧的居室马上焕然一新,年节的气氛就越加浓厚起来。这时,大(父亲)会格外忙,因为庄里有不少人来找他写春联,写天爷地爷的神位牌。
只上过小学的大能写一手好毛笔字,这是他的骄傲,也是我们全家的自豪。每当看到大在各色的纸上留下工整漂亮的墨迹时,我都会从内心里生出对大的无比崇敬之情。
但娘却不以为然,因为来找大写字的人都是庄里关系很好的,一般不表示酬谢,相反在人家等着写字的过程中还要给装烟倒水,饭时甚至还得管饭。
娘的烦恼可以理解,她和婆在灶火里的一摊子已经够烦——做豆腐要一天,做凉粉要一天,别的不说,单是水,每天都要用三四担,其中最花功夫的是蒸馍馍。
过年蒸的馍比较多,少部分自己吃,多的要用来走亲戚。
蒸馍的面头天晚上就和好卧在大锅笸里,几十斤甚至上百斤的面,那可不敢马虎,等面醒到一定的程度就必须上锅,醒不够,蒸的馍硬吧吧的咬不动,醒过头了,蒸的馍又会发酸,白糟蹋了面。
为了把握好火候,婆半夜里都要起来好几次看和的面醒到几成。为了不误事,婆和娘天不亮就生火烧水支起笼屉开始蒸馍。
一锅馍差不多要蒸半个时辰,没钟表计时,婆就燃一炷香,掩上笼盖便把香点着,香燃尽,揭馍的时间也就到了,婆说这叫一炷香的时间。一锅笸面蒸完,已经到了后半天。
既蒸馍又煮饭,灶房的烟火一直不曾停息,攒了一冬的柴眼见着折减了大半,楼栏下的竹席上白中泛黄的大蒸馍却摆得层层叠叠满满当当。
为了增添更多喜庆,婆还会拿一种用高粱秆扎的图章蘸着红颜料在刚出笼的馍馍上印下两三朵小花,艳艳的,漂亮极了。娘和婆彼此相帮着,说说笑笑,活儿干得很愉快。
到最后一锅时,她们又备好了馅儿,要加蒸两屉包子。如果有多余的面,婆或者娘还不忘给我做个鸟雀样的馍馍蒸在笼屉边上,她们说那是“鸽子”,这“鸽子”有脑袋有身子,有用黑椒子装的眼睛,好几天了我都舍不得吃。
腊月三十这天,事最多。
大喝完面茶就开始糊灯笼,糊了大灯笼再糊小灯笼,大灯笼要挂在门头上,小灯笼是专给我提着玩的。
灯笼的骨架都是木制,呈长方体结构,大用白色油光纸糊住灯笼的侧面,再贴红色剪纸装饰,灯座下还要吊上彩色的灯穗,真是足够漂亮。
等大刚糊好我的小灯笼,我就迫不及待地想提一提,但还没怎么过瘾大就说:“小心别把纸弄破了,等晚上过年时再提,晚上里面把蜡点着才像灯笼哩。”晚上提就晚上提,反正没人跟我抢。
大往堂屋门上贴对联的时候,我看得也很认真,看着看着就问大,那对联上写的是啥字,大指着给我念一遍,我也跟着念一遍。
午后,爷开始挂家谱(家谱是按辈分设置着祖先牌位的一种挂图,为了便于长期保存,家谱一般绘制在布匹上)。
平时家谱都是卷起来存放,现在爷小心地把家谱打开,在堂屋上席的墙上直溜溜地垂下。
对那些陌生的祖先牌位,我并不感兴趣,我喜欢的是两边的二十四孝图,对这些图画,爷会不厌其烦给我描述其中的故事,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有“刻木事亲”、“哭竹生笋”和“卧冰求鲤”等。
挂好了家谱,爷就给家谱点灯上香,说老先人也要过年么,对了,还要上坟,我们的坟园比较远,要早些去。
负责上坟的是二爸,我说我也想去,二爸说他把我带上,二爸骑自行车,我提着上坟用的香蜡纸钱坐在自行车后座上。
走完了沿河的大路,到进沟爬坡的地方,二爸就把自行车放在路边,然后我们徒步行进。
尽管二爸是我的父辈,但他跟我相处常常很随便,一路上我们说说笑笑显得挺和气。
到了坟园里,二爸一边教我如何点香燃蜡如何往一个个墓门前插放,一边告诉我每座坟的主人及其生前概况,没墓碑的大略说一说,有墓碑的还要蹲在墓碑前指着碑文给我讲。
坟上完了,要放点炮,但我胆子小不敢放,二爸就鼓励我:“小炮没事,放地上点,点着了马上把脸和身体背过。”
噼里啪啦,一串炮眨眼间就响完了,惊得树上的麻雀成群地向远处飞去。
返回时,天已经快黑了,沿途望见到处的坟园里都是上坟的人,爆竹的炸响声不绝于耳,溅开的火光与坟前的烛光交相辉映,正是上坟祭祖的高峰期。
村庄里家家门前都挂起了花灯笼贴好了红春联,喜气洋洋,年饭做得比较早的都开始打发孩子给左邻右舍端饭。
有些孩子刚把碗放下就从兜里摸出一支“窜天猴”点上,嗖的一声“猴”便冲向空中迅速炸响,火炮声笑闹声此起彼伏。
到家时,娘和婆已经煎好了两大盆面疙瘩,还有一盆面果,饭是少有的蒸饭(米饭),菜也有好几种,比平时丰盛得多。
吃完饭,天完全黑了,我闹腾着要提灯笼,让爷给我在灯笼里点蜡,爷点了一支蜡小心地插在灯笼底座上,还叮咛说:“注意提端,走慢点,不要让火焰烧了灯笼上新糊的纸”。
然后爷在门口的大灯笼里也点着了蜡,灯笼周围一时就光亮起来,让人觉得快乐又幸福。
接着爷又到上席里给家谱点灯上香,到门口给天爷点灯上香,到灶台前给灶爷也点灯上香,爷说今晚灶爷要回来,这也算是迎接灶爷,所以灶台那儿,面疙瘩、面果,还有供茶,能献的都献上了。
我提着灯笼从这个屋串到那个屋,见人就炫耀:“看,我有灯笼!”
二爸和碎爸却只管围着收音机调台,说今晚的节目好,我却似懂非懂,只听得里面又说又唱,挺热闹。
而大竟准备要念一卷灶经,说那次我身体不好曾给灶爷许过经愿,现在正好到了还愿的时候,大还说应该让我跪香。
我不知道跪香是干啥,大说就是在他念经的时候拿一支点着的香跪在灶前面。这个简单,我马上答应了。我跪在一把放倒的笤帚上,盯着烛光中的灶爷像,听着大咕叨咕叨念经。
夜色渐渐浓重下来,各家放炮的声音不断响起,我就不想跪香想放炮。大瞪了我一眼说,去吧!
爷看着我放了一阵炮之后,大把灶经就念完了,厅房里听收音机的二爸和碎爸把收音机也关了,爷拨弄着火盆里的火,又加了块炭说:“今晚过年,不能睡啊。”
我问爷:“那你就一直烤火到天亮吗?”
爷说:“是啊。”
我说:“我不行,我瞌睡了就要睡。”
婆走过来摸着我的头说:“云娃,你爷能坐了让你爷坐去,我们婆孙俩暖炕(暖炕,在热炕上休息)。”
爷也让我先睡,我就上炕了。临睡前,娘把新衣服新鞋放到我枕头边,交代说明天早上起来就可以换上,我欢喜得不得了。
谁家还在放炮,而且是大炮,声音惊天动地的,我佩服那些人的胆量,那么大的炮都敢放。
喧闹的空隙里隐隐约约听见大在底屋弹四弦琴,弹的曲子我娘会唱,好像叫《八月桂花遍地开》。
整个三十晚上都有人放炮,断断续续地一直到了凌晨。
天亮前炮声越加稠密起来,朦朦胧胧地听见婆感叹说:“这些给天爷烧纸的人真是早啊,觉都不睡。”
我睡起时,大人们已经忙开了。娘烧早茶,大和二爸相继给家谱点灯,又给天爷烧纸。碎爸担了一回水刚把水担放下。爷扫着院坝,婆扫着屋内,但扫到一起的尘土和垃圾都在不显眼的地方堆着而没有倒掉,婆说垃圾要等到初五早上才能倒,否则不吉利。
娘看我起来了,就给我安排说:“过年了,去给你爷和你婆磕个头。”
我很听娘的话,立马跑过去,也不管地上干净不干净,扑通一声就朝爷和婆各磕了一个头,嘴里还说着:“爷,我给你磕头了,婆,我给你磕头了。”
爷和婆很开心,一边说着祝福我的吉利话,一边给我一些压岁钱,我心里真是比吃了糖还甜。
喝完茶时间不长,路上就有了来来往往走亲戚的人,都背着背篼,背篼里多数是蒸馍,还有一些用纸包的茶叶或者食盐,酒和罐头之类还很少。
你来,我往,交流着情感,也交换着礼品,走来走去,难免会发生自家的馍馍转了一圈最后又回到自家的现象。
家里来拜年走亲戚的客人,我喜欢,因为可以听大人们天南海北地乱侃。跟大人去给亲戚拜年当客,我也喜欢,因为好吃好喝还有压岁钱。这种忙乱而欢喜的走亲戚活动总要持续到正月十五左右。
因为是年节,每个人都想热闹开心一下,所以白天走亲戚,晚上庄里相熟的人就会凑在一起打牌、喝酒、唱唱书,自娱自乐。
我喜欢的是听唱书。唱书是一种说唱曲艺,唱本都是手抄流传,表演唱书的人以唱为主,时而夹杂说白,可以有琴鼓伴奏,也可以轻敲碗碟和之,全凭故事情节吸引听众。
大就会唱唱书,但只在家里唱,而且只有来了远客,又好这一出的,大才会露露身手。
晚饭已经吃过,娘在火塘里生起火,说她给我们烧茶,让大唱唱书,客在火塘边坐下,我们陪客的也坐下。大唱《梁山伯与祝英台》,也唱《包公案》,我们常常听得入了迷,心情随着唱书内容的变化而变化,高兴处开怀大笑,悲伤处沉默不语。
一段书还没有听完,娘已经把茶烧好,婆的一罐子黄酒也煮上了劲儿,但娘不让我喝酒,只准许我喝面茶。
娘突然记起还有柿子,就打发我去竹笆子上拿几个烟熏过的柿子在火边烤。火烤熏柿子比肉香,我一连拿来好几个,挨挨挤挤地摆在火塘边。
娘说:“簸箕里还有柿饼,也拿些来么。”
我却嫌柿饼没柿子好吃,还发话说:“这几个柿子都是我的,谁也不能吃。”
娘就训我:“多金贵的东西啊,留了半竹笆子哩,看你能吃多少,烤好了一人吃一个。”
头顶的楼板上,老鼠在打架,弄得哐当哐当响,但猫却只管蹲在我脚边烤火,婆就骂猫懒得不像话,客却笑着说:“猫也爱听唱书么。”大家就都笑了。
大正在唱“包龙图夜访阴司,断案如神……”碎爸就冒出一句:“听走亲戚的人说,大南沟的社火这两天要出灯啊!”
“不知道耍得好不好。”二爸也搭话了。
爷说:“如果是大南沟办的社火,估计还能看,他们那儿有几个老干家子,前几年耍社火就有名。”
“要看社火了,要看社火了!”我高兴得嚷出了声。
大停下唱唱书:“是不是不好听,都不想听了?”
客人接过话说:“想听想听,好听得很,接上。”大喝了口茶接着往下唱,窗外的夜安静而温馨。
一连盼望了好几天,大南沟的社火终于要来我们庄里耍了,午饭前社火队里放探马的就先到了,把个旗插在我们庄仓库房前的大院坝当中,庄里的几个头号人物正忙着到各家凑集果品钱物,预备着晚上酬谢耍社火的人。
夜幕降临后不久,一阵欢天喜地的锣鼓声便由远及近,人们都说社火来了,我和伙伴们就极兴奋,拉着大人的衣襟催着要往耍社火的场子里赶,大人却不忙:“别急,那锣鼓声是叫人的,离正式耍还要好一阵哩。”
果然锣鼓是伴着“狮子”先去人户里参神了(参神,相当于耍社火的给人户拜年,仪式完成后主人会给予一定的打赏,被参神的通常是当地比较又威望的人家),参神结束后才会正式开始耍社火。
这时候,仓库房前的院坝里早挤满了等着看社火的人,院坝后面的台子上放着一张大方桌,桌上摆着苹果、核桃,还有麻花,中间一个装粮食的升子(升子,装粮食的木制容器)插着香灯火烛,烛光照亮了一些熟悉的脸。
各式的灯笼,还有一部分手电在黑暗中从四面八方涌过来。
社火开始前,先要要场子,要场子的是“狮子”,“狮子”在人群中又踢又咬,足够霸道地亮了个相,原来挤成一团的人就哗地向四周退去,场中间立马让出一块空地,耍社火的场子就腾出来了。
“看灯山,看灯上,看灯山上看灯山”的锣鼓点子一直没停,渐渐让人烦了,终于嘎地止住,庄里主事的人先讲话,说了些啥没听懂,后面一句大概是感谢大南沟的社火耍到我们票草湾。
然后一个打着大旗的站出来当众把旗挥了两下,高声喊道:“大南沟票草湾面对面,隔河望着常挂牵。”锣鼓跟着又响一遍,这人又挥旗又喊:“今天登门来拜年,耍一折子社火莫要嫌。”锣鼓再响一遍,他再挥旗再喊:“别的兵马先站定,耍狮子的上场来。”
昏暗的灯光里,那只要过场子的“狮子”正式登场。在激烈紧张的锣鼓声中,“狮子”圆睁碗口大的双眼,张开尺把宽的嘴巴,身上的饰物叮当作响,十分威武,我有些害怕,大就安慰我:“别怕,那是假的,是两个小伙子撑着假皮表演。”
当我看清“狮子”的四蹄真是穿着黄胶鞋的人脚以后才放松下来。耍“狮子”的手舞灯笼,逗着“狮子”作揖,打滚,卧倒又站起,最惊险的是引导“狮子”快速爬上几张高高摞起的桌子,耍“狮子”的灵活敏捷,撑“狮子”的勇猛无畏,令人震撼。
耍完“狮子”,社火节目还很多,跑马的娃娃可爱,走旱船的渔夫唱腔优美,表演钉缸剧的说词幽默,时不时“捣乱”的笑和尚(笑和尚,社火中戴面具的小丑)动作滑稽可笑……
慢慢地我困了,迷迷糊糊地在大的背上睡去,不知什么时间,几声震耳的火炮把我从梦中惊醒,可是社火已经散场,人都开始返回。
我发现火炮还接连在耍过社火的场子上响着,奇怪的是有人正把那张供着香烛的方桌猛地推翻,好像要闹事的样子。
我问大:“他们咋了。”
大说:“那是送瘟神,社火耍完都要送瘟神。”
社火耍到正月十五晚上就倒灯(倒灯,指社火结束演出),社火一倒灯,年就算彻底过完,各行各业,该干啥还干啥,日子一天天又忙起来,对于年的向往和牵挂只能暂时搁置。
[来源:作文汇https://www.ZuoWenHui.com]
作文汇,中小学生的作文宝库,提供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应用文 、诗歌、小说、戏剧、散文等各类优秀作文范文参考,提高写作能力。
本文分享地址:《我记忆中的过年作文2000字》
https://www.zuowenhui.com/detail/ecMAMENknwD5TxT1.html